
我是英華男校的畢業生,也曾是香港導演會的法律顧問;亦是早期觀看《給十九歲的我》(To My Nineteen-year-old Self) 的張導演「粉絲」,看畢,立刻出 PO 讚許;可惜,事到如今,事與願違,這部電影的朋友們(包括「投訴」和「被投訴」雙方們),似乎沒有適時妥當地處理電影有關的法律問題:唉,一部出色的紀錄片要停映了,是香港文化的損失。整件事情的發展:「好事變壞事」、「牆倒眾人推」。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一齣劇情紀錄片,不是新聞片,於 2022 年已「選擇性地上映」,至大概 2023 年 2 月才「全面公映」,由英華女校畢業的名導演張婉婷執導,她被時任英華女校校長李石玉如委約,拍攝母校重建過程,包括從半山羅便臣道遷往深水埗德貞女子中學的臨時校舍,電影從 2011 年開拍,跨越 10 年時間。拍攝初期,數十名女生面試開始,慢慢地,焦點集中在其中的 6 位,她們各有不同的家庭背景、性格和遭遇;從求學階段,以至畢業後的人生,影片展現她們的內心世界,猶如你、我、他曾經歷過的成長歲月。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從素材大概 30 萬小時,經多年剪輯而成 136 分鐘的電影版本,它不單止紀錄英華女校的重建、6 個女孩子的歲月,更見證了香港在這 10 年間的風雨跌宕,恍如香港人的集體回顧。
在「學校」及「包場」放映初期,電影大獲好評,但當電影被「全面公映」的時候,突然,發生軒然大波,眾人「發火兒」:片中的幾位女同學公開立場,不同意電影公映。有說剪接出來的片段誤導、有說旁白讓她們難堪、有說影片為生活帶來困擾。跟着,單車運動員
李慧詩說也被誤導,不知道被訪問片段並非新聞採訪,而是放在電影裏。最後,另一位身在美國的同學也表態,說她在誤導下(即以為所有其他人也同意),她才會簽署有關同意書。
滿「片」風雨,唏哩嘩啦。
作為一個律師及調解員,我喜歡從「情、理、法」三方面分析一件事情的對錯。不過,作為旁人,今次也很頭痛。首先,先不談事情可能有更「深層次」的矛盾:有人說:因為張導演參加了政府一個「推廣香港新優勢」的委員會,導致一大批人群,利用今次事件攻擊
她,但是,這等事情,永遠沒有表面證據;政治動機,往往是無味無色,深不可測。
從「人情」角度出發:這群小女孩成長了,各有各的生活考慮,到了今天,不想別人知道她們的私生活,這是極可以理解的,是否為了一紙「合約」,要強她們所難呢?更何況,傳聞她們沒有收取任何工資;但是,另一方面,張導演及工作人員,花了超過十年的心血, 來攝製這部動人的電影,是否因為部分人的改變主意,要把全盤東西掃落地上呢?
再來評評「道理」:當年,小女孩少不更事,交由父母或自己同意,簽署拍攝協議,但是,當年的意願,可否經過十年後,繼續成為女孩子們的「金剛圈」?特別是整件事情的性質,不是商業行為,而是英華女校的慈善籌款,然而,事情演變到了最後,變成全港以及全球大型放映;從中,電影院商、發行商或有更多人,可以獲利,這對家長和女孩子們的慈善初心,公道嗎?影片大規模公映後,女孩子們又不是公眾人物或演員,下半生,如何在別人的眼光下生活?另一方面,女孩及家長們,過去應該有很多機會提出「停映」要求,或採取法律行動,但是,他們沒有,最後,卻用社交媒體施壓,公道嗎?
最後,看看「法律」觀點。法律上,主要有關兩個問題:聘用合約的有效性(即未成年人士合約的約束力 enforceability of the minors’ contracts) 和個人私隱收集(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)。
合約法律中,未成年(即未夠 18 歲)人士所簽署的私人合約或家長一同簽署的合約,法院一概不予以執行,除非是屬於例外情況,其中例如情況是「聘用合約」(contract of employment) 。甚麼是「聘用合約」呢?香港這方面的法律,並非來自條例,而是來自「普通法」(common law,即法院過往的判例),故此,所有闡明,並非代表全面;況且,隨着法院在面對不同案情的判決,法律會有所改變。一份合約是否視為「聘用合約」,法院會研究許多因素,例如未成年人士有沒有薪酬?是否從中會接受專業訓練,例如學徒協議?合約是否對未成年人士有所裨益?服務是否必須由未成年人士提供的特別技能,例如當演員?當法院接納是「聘用合約」後,會再考慮其他整體情況, 才執行這些「聘用合約」。律師處理這些聘用合約時,一般會找家長及未成年人士一同簽署,但是,據說在此事情上,有些協議只有家長一方簽署,也許,這便成為一個法律缺口。
這次合作,本質是為了慈善籌款而拍攝的紀錄片,大家最初只想「好心做好事」,女學生及家長們,為了學校,願意犧牲小我,公開私生活、家庭狀況,甚至成長期間出現的苦況,而且,聽說女生們沒有任何報酬,而合約寫明「版權屬於英華女校」,故此,她們當時相信校方會適當處理電影的放映,家長及女生才放心簽署協議。目前表面結論:問題的法律文件應該並非甚麼聘用或僱傭合約,因此,所簽署的合約,應該不屬於法院可執行的 contract of employment 性質。
最後,讓我討論另一法律:家長或同學所簽署的,是否一份「使用私隱的同意書」?
法律上,新聞採訪需要,而又符合「公眾利益」(public interest),可以不經當事人同意,行為違反個人保障私人的意願。六、七十年代,美國和越南的戰爭中,記者拍到小女孩潘金福裸體逃離着火家園的照片,並視為歷史上最佳新聞照片之一。但是,《給 19 歲的我》, 並非新聞報導片,故此,享用不到這種法律特權。
聽說:在今次事件中,有些家長或小女孩簽署了一份同意書,願意把私生活公開,那麼,四個法律問題來了:
第一,當小女孩長大了,這份《公開私隱同意書》是否仍然有效,特別是她們當中,有些沒有親自簽署過這份協議?第二,但當有些女學生長大後,依然參與拍攝,這等行為,是否等同她們願意在未來繼續公開私隱呢?第三,公開私隱的許諾(consent),法律上是可以中途撤回的(但不影響之前 consent 的有效性),外傳有些女生在過程中,已經抗拒拍攝,這是否等同「明確撤回同意意願」呢?第四,根據《私隱條例》,若使用私隱的目的有變(例如最初只是協議「校內」或「私人場合」才能播放,但是,後來演變成「商映」),那麼,必須再得到當事人的重新明確同意;影片組方,有沒有再找女孩們簽署一份完整的私隱同意書?
最新報導:私隱專員已主動介入調查,保障當年未成年女孩的個人資料私隱,查明在今次事件中,有沒有被違反意願地被使用?要影響一個公眾關注事件的結果,普遍有 3 個手段:第一,是打「輿論戰」,利用 power 去拗手瓜;第二,是訴諸法律,去部門投訴或打官司,以 law 先行;第三,便是雙方坐下來,使用睿智來和解(conciliation)。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是一部優秀的好電影,有能力啟迪香港人對生命的看法;我誠心祝願:各方可以坐下來,用第三個 conciliation 方法,而不使用 power 或 law 來解決;讓影片重見天日,不會從此消失,全港再能夠再欣賞張婉婷導演的心血作品!
(文:李偉民律師)
(以上僅為嘉賓觀點,不代表本號立場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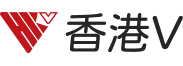



快來分享你的看法吧